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研究(第四章第一节)
发布时间:2025-03-30 20:2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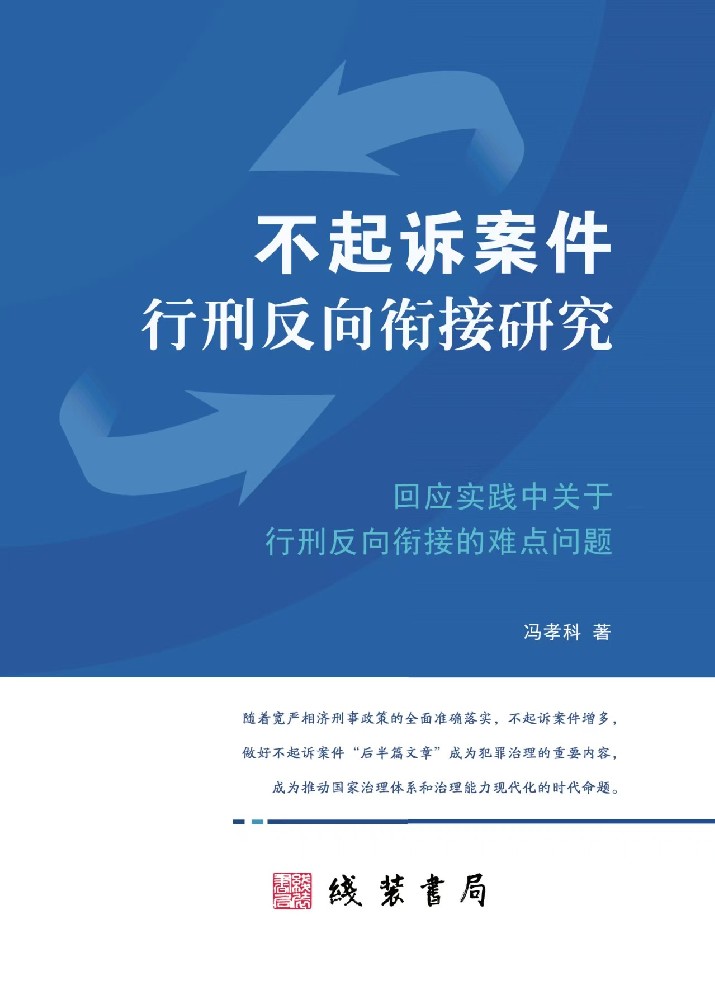
第四章 不同类型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审查要点
如前文所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本书将我国刑事案件的不起诉类型划分为相对不起诉、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特殊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五种不同的法定不起诉类型。下面,我们结合有关法律规定、法理以及实践中的做法,分别对各类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时的审查要点进行探讨。
第一节 相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
相对不起诉在不起诉案件中占据绝对比例。以湖北省为例,2021年至2024年4月,湖北省检察机关经审查作出不起诉决定81960人,不起诉率为28.4%,其中88.7%为情节轻微不起诉。(83)全国的不起诉率及情节轻微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所占的比例,基本上也处于这种状态。因此,全面、准确把握相对不起诉案件的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在刑事检察工作中,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主要引用的法律条文一般是《刑法》第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而该两条也对行刑反向衔接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根据这两部法律有关条文规定,全面、准确把握相对不起诉的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要求,首先要明确以下问题:一是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性质问题,《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内涵是什么,尤其是该条规定的“予以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二是在理论上,相对不起诉案件与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等不起诉案件在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时有什么异同。
一 、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性质
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是指《刑法》第37条规定的,司法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直接适用或者建议主管部门适用的、替代刑事处罚的处置方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对于包括“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内的这些处置措施的性质,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也有的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这些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性质是什么,都不影响检察机关在实务中开展相对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在此,作一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目的是拓宽一下检察人员的工作视野和思维方式。
(一)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性质的认识比较一致,大多认为该条规定的包括“予以行政处罚”在内的处置措施,均是刑事责任的一种实现方式,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
刑事法学界的通说认为,“非刑罚化”是现代刑法观念的一次重要变革,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一种辅助方式,是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措施。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刑罚是一种并列的、互斥的关系,不能将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归为刑罚的一类,二者应当统一于刑事责任之下,是刑事责任实现的不同方式。(84)也就是说,刑事责任分为刑罚和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和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种类即为《刑法》第37条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既然非刑罚性处置措施设置于《刑法》,那么在刑法理论上就具有特定含义:当事人的行为以构成犯罪为前提,只是相对不起诉或定罪免刑而已,所以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一种非刑罚的刑事制裁,其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在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上均有所不同。
因此,即便《刑法》第37条明确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这里的“行政处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责任。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处罚措施都是当事人犯罪后承担的结果,因此,该条规定的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不是一般的批评教育;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也不是一般的民事责任;而予以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当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责任。
有的刑法学者还以普通盗窃案件为例进行了说明。如果当事人的盗窃数额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这里的拘留当然是行政责任。但如果当事人盗窃的数额达到追诉标准构成犯罪,最后因情节轻微对其相对不诉,然后通过行刑反向衔接移送公安机关予以拘留,若把这种拘留理解为行政责任,那么就意味着对构成犯罪的当事人,只让其承担了“行政责任”,没有承担“刑事责任”,这种理解陷入了罪责刑不一致的困境中,在法理上显然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在相对不起诉案件反向衔接中,如果被不起诉人最后被予以行政拘留,那么这种拘留虽然与普通的行政拘留形式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总之,《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中的“予以行政处罚”不是行政责任。
(二)可视为行政处罚
也有观点认为,《刑法》第37条规定的“予以行政处罚”,一定程度上讲,可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在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实现行政法与刑事法之间的秩序和谐,从而为法律规制对象提供一个稳定而可预测的完整规范。
因此,在相对不起诉情形下,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犯罪情节轻微被免除了刑罚的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了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只是法律后果中的一种。如果对行为人不施加任何法律责任,则有违行政犯的从属性与法秩序统一原理。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多样的犯罪情形,简单施加刑罚并不一定能够取得良好惩治效果,对于部分情节轻微的犯罪,予以刑罚则过重,不承担法律后果又无法有效防止再犯,这就需要国家或者司法机关对当事人责任承担方面作出一个平衡。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替代性责任追究,对于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给予非刑罚处罚,实现不起诉后刑事责任的行政责任方式承担。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法律责任一般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实施违反行政法规定的义务的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追究行政责任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叫行政处分,另一种叫行政处罚。(85)诚然,相对不起诉案件中被不起诉人的违法行为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构成了犯罪,但这种涉嫌犯罪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且符合行政法规定的给予处罚的标准,特别是当事人在接受处罚或者承担法律责任时,是由行政主管机关依照行政法的规定予以实施的。既然当事人接受的处罚是一种行政责任,那么这种处罚当然可以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
具体到《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可以采取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人民检察院宣布不起诉决定的同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其中,“训诫”是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谴责的教育方式;“具结悔过”是检察机关责令被不起诉人采用书面方式保证悔改、不再重犯;“赔礼道歉”是检察机关责令被不起诉人向被害人或者相关人员表示歉意的教育方式;“赔偿损失”是检察机关对于因被不起诉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责令被不起诉人给予被害人一定经济赔偿。二是由检察机关移送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根据《刑法》第37条规定,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提出行政处罚的建议(意见), “移送行政主管机关”处理。也就是说,给予被不起诉人的具体行政处罚是由行政主管机关自身决定并适用的,是否处罚、适用何种类型的行政处罚都是由行政主管机关在进一步查明违法行为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独立作出决定。那么,既然这种“行政处罚”最终是行政主管机关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决定,且由行政机关予以执行,那么这种处罚当然是行政处罚。
二、相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已经构成犯罪;二是这种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也就是说,在相对不起诉案件中,被不起诉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检察机关在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中,主要考量的是予以行政处罚的必要性问题。一定程度上讲,实践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行刑反向衔接,在不考虑其他可不予行政处罚因素的情况下,一般是以移送相关行政主管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为原则,以不移送为例外。
具体而言,既然相对不诉是构罪不诉,绝大多数违法犯罪也是一种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且刑法上的不法行为、不法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据的合法性要求等规定,均远高于行政责任方面的法律规定。那么,在有明确的行政法律依据对被不起诉人的违法行为能够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时一般不对案件的事实、证据等进行审查,即一般不审查应不应该罚,重点审查可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也就是综合多种因素考量对被不起诉人需不需要处罚。
比如,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办理的王某峰等三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相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2022年6月11日,王某峰参加2022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安排隋某芝组建部分参加考试人员微信群,由参加考试人员用手机将试题拍照发到微信群,隋某芝、王某梅在考场外查找答案发回群内供参加考试人员抄写。王某峰在考试现场被公安民警抓获。2022年10月18日,公安机关以王某峰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峰、隋某芝、王某梅的行为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于2023年8月15日依法对王某峰、隋某芝、王某梅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烟台市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认为应当对三名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遂按照行刑反向衔接规定,将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办理。烟台市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应当给予有关当事人行政处罚。
2023年8月15日,烟台市检察院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意见,建议根据《刑法》第37条、《行政处罚法》第27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第31号令)第8条之规定,对王某峰组织考试作弊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同年8月24日,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王某峰作出“2022年度山东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并长期记录”的处理决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抄送检察机关。
通常情况下,构罪的违法行为一般都是情节严重的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检察机关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在有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原则上是可以直接将被不起诉人移送行政主管机关给予其行政处罚的,但我们要注意总结实务中相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的问题, 一方面是“不诉了之”,即后续处罚措施的缺位,不刑不罚、应移未移、应罚未罚,从而造成的“处罚倒挂”问题;另一方面是“不刑就行”,对于所有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均不作区分、不作考量,绝对化地提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过度地进行行政处罚。目前,检察机关高度重视相对不起诉的“后半篇文章”,“不诉了之”的现象有所改善,但“不刑就行”的现象需要引起注意 。
注释:
(83)参见《湖北检察机关交出轻罪治理高质效“答卷”,3年以来81960人被不起诉》,《楚天都市报》2024年5月7日。
(84)参见冯军、梁根林、黎宏:《中国刑法评注》,202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85)参见全国人大网“法律释义与问答”。
(86)案件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三,参见《中国行政 检察发展报告(202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者 冯孝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