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冯孝科著
发布时间:2025-03-31 20:5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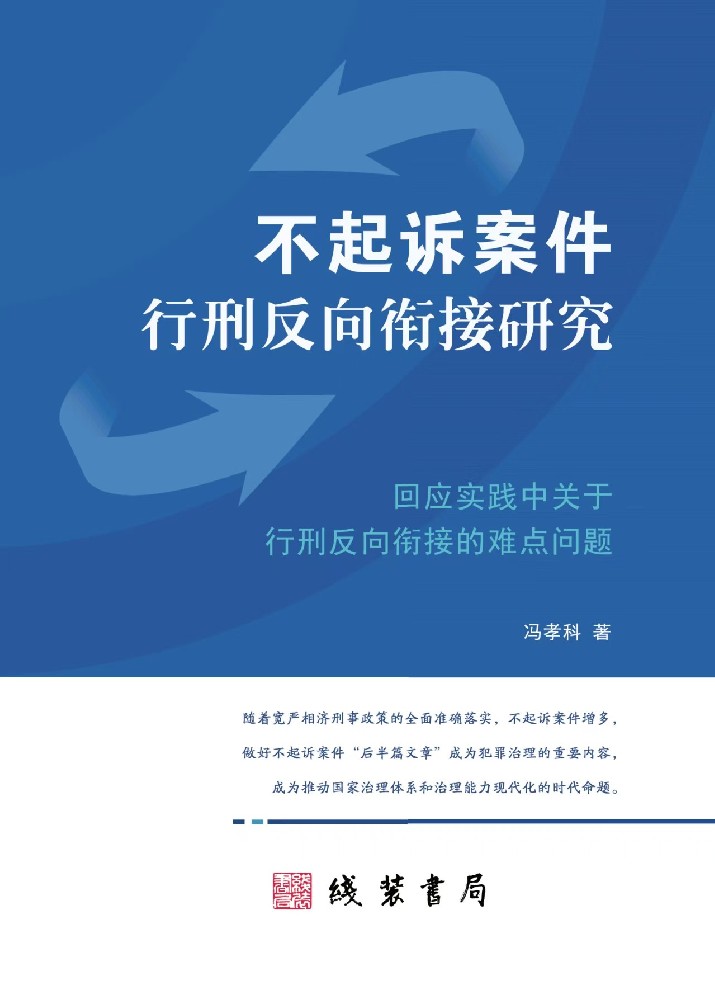
第四章第二节 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
绝对不起诉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诉至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处理决定。存疑不起诉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与相对不起诉案件中,被不起诉人的构罪不诉、构罪免刑的情形不同,对于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案件而言,在违法性质上,被不起诉人并没有构成犯罪,其行为是否构成违反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并需要予以行政处罚,尚待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中,判断是否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时,不应受犯罪标准的影响,而应以衡量其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为重点。也即既要审查可罚性,又要审查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同时,在实务中,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行刑反向衔接也具有各自的特征。
一 、绝对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
在绝对不起诉(法定不起诉)中,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的规定,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该法1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依法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本身只规定了一种绝对不起诉情形: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而《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了六种绝对不起诉情形,分别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法律规定的七种绝对不起诉情形中,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以下三种,检察机关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一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在该种类型的绝对不起诉案件中,虽然被不起诉人的违法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但这种“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只是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不构成犯罪,其违法行为很可能存在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情形。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注意审查相关的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规定,综合判断是否需要由行政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比如 ,N省Z县检察院办理的陈某等四人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法定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陈某等四人在其出租屋内进行网络直播带货,将购进的加工处理过的翡翠 (B 货)充当天然翡翠 (A 货),对外销售给张某,销售金额11000余元。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积极退赃。Z县检察院研究认为,陈某等四人在网络直播间销售以次充好玉器属于销售伪劣产品,但其销售金额尚未达到我国《刑法》规定的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的五万元的追诉标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最终对陈某等四人作出法定不起诉处理决定。其后,该县检察院 刑事检察部门将案件移送本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陈某等四人在网络直播间违法销售金额一万余元,没有达到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追诉标准,对其作出法定不起诉处理决定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但当事人在产品中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向Z 县市场监管局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市场监管局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对陈某等四人予以处罚。市场监管局采纳检察意见,对陈某等四人依法作出分别罚款10000元,并没收违法所得8000元及涉案伪劣玉器的行政处罚。
二是“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形。追诉时效是《刑法》所设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所需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间内,司法机关享有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权利。一旦犯罪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期限,那么司法机关不得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已经启动追诉程序但尚未完成的案件,其相关流程应被依法终止,若案件处于审查起诉环节,则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考虑到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进行追诉的时效一般比行政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的时效长,因此,对于犯罪行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一般情况下,不宜再提出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三是“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情形。关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我国《刑法》中规定有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普通侵占罪等五种犯罪。《刑法》中规定的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能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自愿不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刑法不予处理,但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由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近亲属告诉的案件,按照刑法规定处罚。因此,对于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形,根据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需要制发检察意见。关于这类不起诉案件的具体情形,根据《刑法》规定,本文将其分为一般情形、特殊情形和例外情形。
一般情形下,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告诉的,刑法才予以处理,他们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司法机关不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已经追诉的,应当撤销案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告诉或者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行为,表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放弃了权利救济,不希望通过国家公权力让对方接受处罚,因此,从尊重当事人权利行使角度出发,检察机关以不开展行刑反向衔接为宜。
特殊情形下,因被害人的人身受到限制、精神受到控制而不能告诉,致使犯罪人逍遥法外,为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害人的近亲属、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依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此种情形下的不起诉案件,若符合行政处罚条件,可以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提出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例外情形,指的是因侮辱、诽谤他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国家利益,或者因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或者虐待家庭成员造成重伤、死亡的,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应当依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情形的犯罪,已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这些案件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若符合行政处罚条件,当然能够开展行刑反向衔接。
二、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
在存疑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67条的规定,对于二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案件,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对于经过一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再次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补充侦查必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实践中,对于存疑不起诉的案件是否能够进行行刑反向衔接,提出给予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存在不能够行刑反向衔接及能够行刑反向衔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不能够行刑反向衔接
有观点认为,对于存疑不起诉案件,检察机关不能够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
一是存疑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法律依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存疑不起诉的情形单独规定在该法第175条,绝对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则分别规定在该法第177条第1款、第2款,而对不起诉案件进行行刑反向衔接的规定则是在该法第177条第3款。由此,持存疑不起诉案件不能够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观点认为,由于《刑事诉讼法》177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了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而第3款规定了行刑反向衔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推测出能够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不起诉案件,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2款规定的绝对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情形。因此,检察机关若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没有《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
二是存疑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有违刑事优先原则。此种观点认为,刑事优先原则的实施,旨在确保对犯罪行为的及时、有效打击,防止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从而保障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87)刑事优先原则在处理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时和办理时占据主导地位。存疑不起诉不是刑事案件的终局性处理结果,因此,在刑事案件未了之前就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有违刑事优先原则。另外,对于存疑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若给予了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待司法机关发现新的证据对当事人重新予以起诉并最终确定其构成犯罪后,使得当事人由于其违法行为,分别承担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不公平后果。
应当说,以上观点及理由是有所偏颇的。关于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从法律条文内容看,《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的是补充侦查制度,在立法技术上将存疑不起诉制度规定在该条中,应主要是基于行文逻辑的需要。该条第4款规定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从《刑事诉讼法》整体结构来看,这样规定使得行文更加连贯流畅、逻辑更加清晰,不能据此就认为存疑不起诉不适用行刑反向衔接的规定。另外,在我国的立法中并没有限制行刑反向衔接中不起诉案件的类型,比如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最高检《意见》的规定,都没有对不起诉案件的类型进行特别限制。因此,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法律依据充分。
关于有违刑事优先原则的问题。我们认为,刑事优先原则是处理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案件移送、办理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的规定予以不同处理,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公正和效率。一般情况下,在发现违法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优先给予刑事处罚。然而,这一原则并非绝对,它存在一定的相对性。在具体追责时,考虑到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平衡,行政处罚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优先于刑事追责。比如,当行政执法措施能够快速制止违法行为时,行政处罚也可以优先适用。此外,在处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的情况下,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同质罚相折抵”和“不同罚各自适用”的原则,这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可以相互折抵或各自独立适用,以避免重复处罚或处罚不足的情况。
(二)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审查重点
综上可知,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要求,各类不起诉案件的行刑反向衔接,在办理程序上并没有区别,存疑不起诉案件可以且应当开展行刑反向衔接。但是,基于存疑不起诉案件的特殊性,实务中检察机关在开展行刑反向衔接时,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审查确定。
对于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应当重点审查涉案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是否清楚,在案证据能否达到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等。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案件尚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认为行政违法事实清楚、应当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意见。就案件事实和证据方面而言,存疑不起诉案件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全案存疑。全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情形较多出现在当事人的一次违法行为涉嫌违反单一罪名的案件中。由于构成犯罪的某一要件或者某几个要件缺失,导致无法认定犯罪事实。对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的全案存疑不起诉案件,是否提出行政处罚的意见要结合案件情况全面审查。如果全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般不提出行政处罚的意见;但如果能够查明部分违法事实,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不起诉人主观上有违法犯罪的故意或过失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应当终结审查或者不提出检察意见;若在案证据虽然不能证明当事人构成犯罪,但能够证明违法的,也可以提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比如,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办理的李某某、杨某某涉嫌滥伐林木罪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2022年12月8日,甘肃省嘉峪关市某镇某村委会通过村两委会议决定,对该村60亩集体所有防护林中因为病虫害导致死亡的杨树砍伐后补植。同年12月12日,该村委会主任李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联系杨某某采伐该村10组靠近养殖场附近林场中的杨树,采伐5亩左右杨树后被嘉峪关市林业和草原局发现并制止。公安机关以李某某、杨某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3款关于“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所涉林木系风倒、火烧、水毁或者林业有害生物等自然原因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从宽处理”的规定,所砍伐树木为死树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李某某、杨某某供述及证人证言证明:被伐树木多数系枯死树木,且由于案发现场地处偏远,案发后被伐树桩大部分被村民挖走,已无法确定被伐活树数量和立木蓄积量。城区检察院于 2023年10月17日依法对李某某、杨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将案件移送本院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该院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认为,原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林函策字〔2003〕15号,现行有效)规定: “凡采伐林木,包括采伐‘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损毁的林木,都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擅自采伐的,应当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对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据此,行政执法中,对于盗伐或者滥 伐林木行为,无须区分被伐树木的死活状态,只要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而采伐树木的,即使所伐树木为“火烧枯死木”,依然应当定性为盗伐或滥伐 林木行为,对行为人予以处罚。
2023年10月18日,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向嘉峪关市林业和草原局制发检察意见,建议根据《森林法》第56条、第76条第2款之规定,对李某某、杨某某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2023年12月11日,嘉峪关市林业和草原局按期作出处罚决定并反馈检察机关,决定对某镇某村村委会罚款26088.88元,责令村委会限期补种树苗187棵;对参与砍树的杨某某罚款1650元,并没收违法所得。(88)
二是部分存疑。对于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部分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当事人该部分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可以提出检察意见。比如,在当事人多次、多种类的违法行为中,存在查明的部分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可针对已经查明的该部分违法行为审查行政处罚的必要性,认为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可以提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比如,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办理的王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2022年4月19日,王某某受“张某某”委托在未取得船长适任证书的情况下,驾驶船舶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出发,前往舟山市岱山县长途岛南面海域抛锚,在明知铁块无合法来源手续的情况下关闭 AIS(船舶自动识别装置),从不明船号的货船上过驳铁块1258.88吨,并与上家约定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运费运往福建。2022年4月20日,该船航行至象山县檀头山附近海域时被宁波海警局查获。公安机关以王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象山县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认为,查获前王某某将手机及上家所给手机卡丢入海中,致使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王某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象山县检察院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于2023年8月17日对王某某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其后,承办案件的刑事检察部门将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办理。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虽然无法认定王某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可以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检察机关另查明,王某某除存在违法收购赃物嫌疑的货物外,还存在未取得船长适任证书驾驶船舶和在航行过程中主动关闭AIS等危害海上交通安全的行为。
2023年8月18日,象山县检察院向宁波海警局制发检察意见,建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第3项之规定,对王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3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4条第2项之规定,对王某某未取得船长适任证书驾驶船舶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2023年10月18日,象山县检察院向宁波海事局象山海事处制发检察意见,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36条之规定,对王某某主动关闭AIS的危害海上交通安全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2023年11月2日,海警部门针对王某某窝藏、转移、代销赃物的违法行为作出拘留十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未取得船长适任证书驾驶船舶的行为作出拘留十三日、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合并执行拘留二十日、罚款一千五百元。2023年11月27日海事部门针对王某某主动关闭AIS的危害海上交通安全行为作出罚款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对该船船长罗某某放任王某某关闭 AIS的行为作出扣留船长适任证书三个月、罚款五千一百元的行政处罚。(89)
注释:
(87)参见刘艺:《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衔接监督机制中的作用与职责》,《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88)案件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五,参见《中国行政检察发展报告(202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2024年出版。
(89)案件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第一批)案例二,参见《中国行政检察发展报告(2023年)》,中国检察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者 冯孝科

